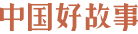中外合拍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在国际纪录片界,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孙书云是一位中国故事的成功讲述者。孙书云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在英国从事独立纪录片制作,其著名纪录片《西藏一年》曾以“罕见的深度”呈现了一个西方人所不知的西藏。近年来,她又涉足中外合拍纪录片领域,先后与中央电视台、BBC等中西主流媒体合作制作了《中国艺术》《喜马拉雅的天梯》《天河》等中国题材纪录片。

“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困扰中国纪录片多年的问题,笔者带着这一问题,先后于2019年7月27日和10月5日在伦敦书云家中采访了孙书云女士,得到了其富有创见的回答。在此将采访整理成文,以为国内纪录片的创作和“走出去”提供借鉴。
一、合作方的诉求决定中国故事的讲述
王庆福:所谓中外合拍是由不同投资者组成共同体,合作完成一部作品,每个投资者都有各自的话语权。您在英国直接和西方媒体打交道多年,请问像BBC这样的投资方对合拍纪录片最终讲述的中国故事会有哪些影响?
孙书云:纪录片跟任何艺术作品一样,是一种创作。既然是创作,那么创作者对于主题的把握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它应该是独立的,而且创作者一定要对这个主题有很大的把握程度,这种创作首先是应该由制片人、监制或者是他的独立公司来进行操作,然后由独立公司为电视台来制作。否则,无论是在哪一种体制下,没有充分的把握力,哪怕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也会走偏。相对于国内纪录片,面向西方的中国故事纪录片在操作上难度更大,因为中外的欣赏习惯不一样。投资方对于中国人的故事历史和背景了解又不够多,除非你的想法比他们好,否则他们没有兴趣来听你的。
其次是资金问题。在西方坚持创作独立的原则之下,投资方还是有发言权的,他们会提出他们希望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纪录片要讲好一个故事的话,首先就是这个故事本身要真实,因为你不可能期待对方替你去做你想要的宣传。但是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强调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去讲述这个故事?这里有很大的表达空间。
最后,在投资者决定了之后,谁来做这个项目?是导演,制片人,还是监制?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当你跟电视台说,我想这样讲述故事时,你的同仁、你的上级都觉得这样讲述是一个好的方法,那么他就会帮助你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样就点到了问题的核心,就是说讲中国故事一定要落实好创作者、投资者、选题三个主要问题。选题要选好是第一步,西方受众期待的不是要了解中国最先进的东西、最光明的东西,西方媒体也标榜自己是将批判作为职能所存在。你不可能希望他突然把过去这么多年的习惯、行业的规矩都抛弃了,来给你去唱赞歌。但他们也不希望一直都在批判,为什么?因为批判容易,建议难。这个东西不对,对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要给人家一条出路,而不只是说这样不好,怎么才能够做得更好是关键。从政府职员到民间的、社会的力量,不同身份的人诉求不一样,问题的关键是谁来做,跟谁做,谁投资。如果每一个都能把握住,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讲好了中国的故事。
二、对创作的尊重是讲述中国故事的前提
王庆福: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您的《西藏一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请问这个成功的奥秘是什么?
孙书云:《西藏一年》最大的成功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来自于我的本事,而是我们的合作者——藏学中心的副总干事格勒博士。记得《西藏一年》拍摄时,他们中心去了人,虽然不是在监视我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看我干什么。他当时就对他手下的人说,书云老师什么都可以拍,最后能不能用是她跟我商量的事情,你不要阻止她去拍。我们拍到的所有东西,无论是去拍班禅喇嘛,还是寺庙被盗,这一系列的事情他都没有查,到最后编辑的时候,格勒博士就提出了一点反对的意见。
这个反对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三集《深冬》一集里,拉巴是最穷的一位主人公,因为冬天没有什么事情做,他就去藏北打工。他喜欢和一帮兄弟一起喝酒,喝完酒之后就跟当地的包工头吵起来了。这一段镜头,国内版没有,但是在国际版上,有包工头还有盖房子的房东打了他的镜头。当时格勒博士在所有的五集当中,对班禅喇嘛寺庙被盗、拉姆医生去拜佛、治不好病、一妻多夫他都没有说什么。唯有这段内容他说,书云你觉得这个有必要吗?我当时就有点惊讶,我说您的意见是什么?他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表现藏族人不好的方面。当时他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因为现场看包工头打得很凶,一个巴掌就扇去了,但是他没有让我们关机,我们的摄影师真的是很沉着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往外赶。但是我还是很惊讶,格勒博士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看得这么重?我想了一下,觉得可以理解他,因为对他来讲,所有的藏族人都是一样的。这样凶狠的形象跟大家想的传统藏族人那种比较仁慈的形象好像不太相符的。怎么能把藏族人看成是这样子?确实,这样的事情在他看来不算太多,但拍出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典型性的东西来表现了。我觉得这是格勒博士非常了不起的方面。
当格勒博士问我放这个镜头是否有必要的时候,我回答说,对一个纪录片来讲,能够去抓住这样的东西确实不太容易。可你说真的有必要吗?那可以没有。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会影响人们对藏族人的一种印象吗?我也觉得不会。因为这个时候是就事论事,拉巴是喝多了,大家是知道的,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去打工来维持生存,其实是展示他的不易。我们的创作队伍,不只我,包括我们英国的制片人,并没有因为这一片段觉得藏族人不好,反倒是觉得他很艰难,他多不容易。
王庆福:如您所说,在讲中国故事之中,不同的制作主体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请问您作为具体创作者,对整部纪录片创作的发言权是怎样的?
孙书云:我不是一个特别急功近利的人,这十年来才做了三部片子,每一部片子花的时间都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我对片子的发言权,其实应该比领导或者是合作方都要大得多。你要对别人有发言权,首先你自己要对这个题材有深刻的理解和激情,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是超出别人的。当然,跟一个很好的导演去合作,他们有很多艺术创作的方式,把这个东西用在某个画面上能够以更好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大家互相讨论的过程。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你不能要求别人尊重你,也不能要求别人同意你的想法,重要的是,你的想法经过很多的思考,确实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同时也确实有很大的操作性。还有就是叙事上故事的独特性,一个好的故事是容易被接受的。
三、不同版本的纪录片讲述中国故事的追求不同
王庆福:《西藏一年》之后,您又制作了《天梯》和《天河》,与以往人文类纪录片不同,《天河》属于自然题材纪录片。《天河》制作了两个版本,国内版和国际版完全不同,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孙书云:国际版《天河》的故事完全从一个国际化的角度,也就是完全从一个自然历史的角度来展示。国内版《天河》主要写的是人,而且范围相对比较小,从雅鲁藏布江源头到中印边界,把这一段做成了六集,基本上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表现方式。
《天河》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主题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来展示新中国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世界公认的。在我们《西藏一年》里,这个成就也反映出来了,无论是包工头、家庭饭店老板、乡村书记、乡村的法师,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成就是夹杂着一些烦恼和挑战的。对我来讲,《西藏一年》,包括《天梯》国际版,其实是把这种问题都反映出来了,所以大家才觉得真实。可是在《天河》的国内版当中,它只是成就。在国际上,《天梯》和《西藏一年》之后,西藏题材纪录片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去发现一个新的角度来让人们了解西藏这个地方。现实是,目前在西藏问题的国际对话上,中西之间没有太多的拓展。依然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让人们了解西藏是有一定难度的。要想新,就要抛开已有的内容。对我来说,自然,就是让人们了解这块第三极独特之处的一个新切入点。我觉得75%的内容应该是动物和植物以及地质的。通过一条河把喜马拉雅南北坡、三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联系起来。大家在江滨,共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西藏文化的另一方面。
选用自然的这个方式,包括地质的这个方式,其实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这样做整体来讲能够把这条江边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江给这三个国家带来的影响表现出来,这是在现代的语境之下,对于西藏的又一次展示,这是纯自然的展示。它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在西藏境内,除了十多年前BBC拍的《野性中国》那里面有一集是关于西藏的野生动物,到此为止就再也没有拍西藏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了。野生动物的拍摄在西方其实是很多,但是在中国并不太多。西方的野生动物拍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一个非常详尽的、对于动物和植物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西方的很多大制作其实是跟着研究组,他们对动物行为的研究,是通过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类似于观察动物的教室进行的,纪录片的拍摄也是通过半野生和纯粹野生两种状态的结合进行的。
四、相互信任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王庆福:中外合拍的过程常是不同制作主体之间力量的博弈,因此使合作方之间达成默契至为关键,那么您在摄制中国故事纪录片的过程中,是怎样克服其中的困难,做到相互信任,达成真正的合拍呢?
孙书云:在这样一个敏感话题和敏感区域里,信任是关键的。不光是国内要信任我们,国际上也要信任我们。凭什么让人觉得你会把这故事讲好,那是因为其一,你以前已经讲过这样的故事,你的团队做过不少这样的片子;其二,就中国的合作伙伴而言,你们所带来的国际资源,你们对选题的把握是前提。信任是基础,但信任不是开始就有的,信任是多次合作的结果。尤其现在,在涉及怎么样才能深入进行国际合作的问题上,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代表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你的投资方能够充分信任你。国际合拍往往都是大制作,其资金来源于不同的投资者,每一个投资者都有一种声音,所有的投资方有平等的权利。
对于我来讲,中方现在在国际合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我觉得现在国际局势越来越有重新回到冷战状态的趋势。这个投资联合制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什么让西方制作机构和中国投资方达成共识呢?《天河》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天河》这部片子整体上所面临的挑战是自然的挑战,但在拍摄中有一个争议,是关于拉萨的。对于国际版《天河》,当时中方并没有说希望把拉萨放进去。因为将拉萨放进去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也许会容易让人感觉含有政治意味。我们当时觉得拉萨还是比较重要,因为拉萨就建在这个雅鲁藏布江上,而且这个城市本身就有着美丽的传说。这里到处都是沼泽,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建立大昭寺,她把寺庙放在那里,能够把水中的各种妖魔都镇住,这个城市才能够建起来,才能够稳定。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了。拉萨不只有大昭寺,还有龙潭湖,还有那个大沼泽,这其实都是江遗留下来的东西。中方当时就没有同意,但是最后领导审片子的时候说,片子怎么都是江滨,都是这么朴素的东西,这没有展示现代的拉萨。这时候重新去做已经晚了,因为所有的拍摄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从那个航拍就可以看出来拉萨它就在水边。所以最后跟央视去商量,我们就选择了素材共用的这种合作方式,从最后呈现的片子看,是一个对整个拉萨的全景俯瞰,里面不仅有布达拉宫,有老式的街区,还有新建的拉萨火车站和现代化的拉萨新区。
拍摄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成为真正的合作者,大家必须有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就是基于把这个片子做好,让所有的合作方都能够基本满意。这个片子制作出来后在德国、法国、奥地利播出,其中在奥地利收视率达到27%,非常高。这就奠定了奥地利国家电视台跟央视接下来的几个大项目合作的基础,有了后续的《长城》的合作,《丝路上的秘密》的合作。所以我认为,《天河》真正能够把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最标志性的东西介绍出去,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
五、创意与表达是讲好中国故事问题的核心
王庆福:《天河》之后,目前您正在运作大型自然类纪录片《中国国家公园》,这一纪录片的合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孙书云:国家公园这一项目计划在三年里,建成一个比美国耗时150年建成的国家公园面积还要大的公园,它借鉴了很多国际上的经验,同时又有中国自己关于保护地质、生物、植物和人文的独特文化,非常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必须要给他们找非常好的国际合作伙伴,能够把中国的东西在国际上传播出去。我们发现,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海拔在3500米以上,这里人很稀少,动物是为王的。近年来,这里的一些地方开始开矿。而国家公园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动物的生存,保持动物为王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海拔在2000到3500米的四川和湖北,可以说是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又是中国森林和水源最多的,在这里动物与人开始争夺生存权,大家要共生的话,可能都要退一步。所以就退耕还林,把所有的森林再次重新结合起来,那动物就有更多生存的地方,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平衡。东南沿海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动物就完全地开始适应人了,比如像武夷山是中国自然与人最和谐的一个地方之一,它其实完全是人造的山了,都是茶园,是自然和人文双遗产。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展现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在这样的地方种茶,而茶又是一个全球化产业的东西,它依然能够与自然达成平衡,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模式。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创意:动物为王和人为王,但是人为王的前提是要尊重自然。然后是中间地带,人与动物之间通过比较微妙的博弈,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把这个创意做成提纲给了央视四套,然后给了BBC,央视一看就说,这方案很聪明很简单,因为他可以看到他要的东西。BBC也觉得这挺神奇的,中国人原来是这样子,中国原来有这么大一块地方,在它的西部就根本没有人居住,中间这块是人与自然在博弈,并非一定要人去战胜自然。这个国家公园的确立,就是人开始退让,动物开始进军。但是这也不是动物胜了,因为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人类建造了太多的工厂,太多的主题公园,占地确实很大,使一些野生动物失去它们的栖息地,所以就要退耕还林。这样的冲突和解决也几乎只有中国才能做到。国家公园就是一个当务之急,是为子孙保留青山绿水,它中间有很大的牺牲,有很大的痛苦,有很大的博弈,那么这个创意我觉得就不是一种对于中国目前主导环保的政策图解。大家都知道环保的重要性,不是容易的,要有代价。所以在设计这部纪录片项目的方案中,我们既展示了中国独特的地貌和人文的价值,同时又展示了这种国家公园建立的重要和不易。这样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
六、与受众对话是讲述中国故事的最终目的
王庆福:关于中国故事,西方纪录片从他者视角出发,惯于一种批判的眼光。而中国纪录片惯于正面宣传,两种不同诉求的制作主体合作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孙书云:对西方来说,他们教育当中就是强调批判的态度,因为批判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沾沾自喜的话,你就没有什么要改变的了,我觉得这是体制的一种DNA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在改变。比如像上海纪实频道,他们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其实做得真的挺好的。他们从平凡人当中看到喜悦、追求,展示生存的一种状态。大家都在开始慢慢地找一种共同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毕竟要面对这么多的观众,不是政府给你钱,就让你去讴歌,政府也要走市场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家公园》是挺好的一个案例。我们之所以在做环境保护这块内容,拍摄相关的人和组织,就是希望通过他们来发声。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只有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才可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