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9日,中国第一座自行勘察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材料的“争气桥”——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这座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举全国之力耗费8年时间建成,是中国东部地区交通的关键节点,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江苏的文化符号、共和国的辉煌。
大桥由正桥和引桥两部分组成,正桥9墩10跨,长1576米,最大跨度160米。通航净空宽度120米,桥下通航净空高度为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24米,可通过5000吨级海轮。大桥上层为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连通104国道、312国道等跨江公路,是沟通南京江北新区与江南主城的要道之一;下层为双轨复线铁路桥宽14米、全长6772米,连接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干线,是国家南北交通要津和命脉。
今天的中国,
既能造世界上最长的桥,
也能造世界上最高的桥,
虽然路桥工程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
不过提起“大桥”二字,
能称为共和国记忆的,
恐怕还得数南京长江大桥。

这座大桥,
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对桥梁建设者来说,
它是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大桥;
对八零后九零后来说,
它是课本上需要全文背诵的课文;
对岁数更大一点的中国人来说,
它是岁月的写照和时代的缩影。
大桥波澜起伏的身世,
绝不比大桥本身的壮丽逊色半分。
故事,
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起……

奇迹,就是举步维艰,
他们却创下许多“中国第一”。
1960年,梅旸春来到浦口,
成了大桥的第一任总设计师。
开工初期,工地士气方盛,
设备齐全,材料充足,
梅旸春不分昼夜指挥,
险情被他一一化解。

图/第一代大桥建造者
然而,热火朝天的状况没持续多久,
国家就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
大批工程下马。
梅旸春不顾病况,多次奔赴铁道部,
“希望在桥墩出水后停工,
否则几年辛苦付诸东流”。
周恩来总理发话,
特批大桥继续招工、购买设备,
施工虽得以继续,速度还是慢下来。
不久,梅旸春因高血压病重,瘫痪在床。
1962年早春,组织决定送他到北京休养。
行前,他最后一个愿望是到工地看看。
这一看,成了他与南京长江大桥的诀别--
当晚,梅旸春老泪纵横,对妻子说:
“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恶呀,
不让我建完大桥!”
凌晨他突发大面积脑溢血,
再也没有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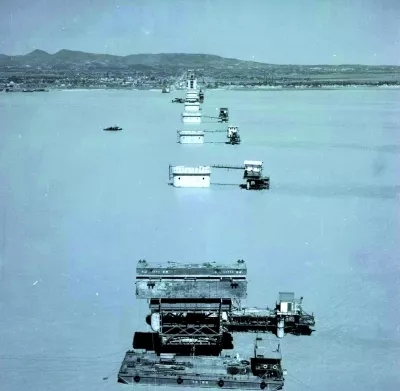
图/1965年11月,正桥9个桥墩前后历时7年多得以建成。
1964年9月,
大桥工程又遭遇建设中的最大危机:
在洪水冲击下,
5号和4号桥墩的锚绳先后崩断,
自重6000多吨、七八层楼高的沉井
在激流中作最大幅度60米的周期性摆动。
一旦主锚崩断,不仅大桥面临着沉井倾覆、
桥址报废的危险,下游百姓也要遭殃。
建桥工人冒着生命危险,
连续抢险近两个月,
最终克服了沉井摆动,使大桥转危为安。
工程施工一波三折,处处却有自力更生,
也让大桥创造了中国的“许多第一”。

图/在那个年代出生的“桥二代”许多都叫“长江”“大桥”,有的干脆就叫“桥墩”“钢梁”“铁柱”。
南京长江大桥共有150多万个铆钉,
铆钉连接工艺就出自南京长江大桥
最后一任总工程师陈昌言的创意。
这种办法就是在桥上点鼓风机的炉子,
把生铁烧红,这边甩上去,
那边工人接过来就迅速插进去,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无缝焊接技术。
虽说是土办法,但150万根铆钉
最终把大桥的钢桁梁结结实实联在一起。
架梁的两年多时间里,
陈昌言几乎每天在梁上爬上爬下,
来回巡视,时刻提醒工人:
铆钉要烧红烧透,进孔要正,
开裂弯曲的一定要重来。
如今半个世纪来,
桥上150多万个铆钉返修率极低,
几乎可以不计。

图/1968年10月1日,第一列火车通过南京长江大桥。
1991年,陈昌言逝世,按他的遗愿,
家人将他安葬在浦口的象山湖边,
正对着长江大桥。

有一种感动叫死后
也要守着南京长江大桥长眠,
有一种付出叫几十年如一日,
有一种精神叫做自力更生,
有一种技术叫中国技术,
有一种力量叫中国力量!
南京长江大桥,
关于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
记录仍将继续。
网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