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参与了每一次对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具有巨大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导弹、人造卫星、登月工程。

2006年6月11日,航天技术和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逝世。杨嘉墀,一个普通人很少见到的名字,却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863”计划四位倡导者之一,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牵头建议者。
他几乎参与了每一次对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具有巨大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导弹、人造卫星、登月工程。
几乎在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会高瞻远瞩地及时提出重大建议……
嘉称连连丹墀生辉
因为他留过洋,更因为他姓杨,人们都叫他杨先生。他的学生这样叫,他的同事、朋友也这样叫。逆境中不能明着叫,人们就背地里悄悄地叫。人们都觉着这样叫比叫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总”、什么什么院士要好听。透着敬佩呢!
他的名字叫嘉墀,是祖父杨晓帆给起的。嘉者,善与美也,如嘉谋,嘉言,山泽多藏秀,士风清且嘉。墀者,台阶也,班固赞西都的赋中有这样的词句:玄墀扣砌,玉阶彤庭。
祖父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么个名字?说起来应该是源于生活,源于杨晓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杨家祖籍原本河南,是无情的黄河水泛滥后将他们逼到江苏最南端紧傍太湖的小镇震泽。杨晓帆年未弱冠,便承继父业,与丝织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度春秋,惨淡经营,竟成了震泽的首富。“纺织娘”、“金孔雀”丝曾风行于法国、瑞士。在20世纪20年代与日本丝进行的殊死较量中,他深悟复兴丝业必须自己培养人才。在任丝织业会会长时,出巨资兴办了一所“丝业小学”,为的是给儿孙们留下一片成才的绿地。嘉墀出生了,老人又把无限希冀寄托于小孙子身上,期望他能一步一个台阶地成为有用之才,更期望他能成为国家繁荣强盛的一个石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出一份力。如今,80多年过去了,回首看一看,于家于国,嘉墀都没有辜负祖上对他的殷殷期盼。“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是大诗人杜牧到乌江亭楚霸王项羽自刎处,触景生情后发出的慨叹。而同为江东子弟的嘉墀,却不需要这样的诗句。
丝业小学太小了,他要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他乘乌篷船行了一天一夜到了大上海。上海交大也太小了,满足不了他对知识的渴求,于是他又乘海轮,离开了中国。哈佛大学也还是太小了,无情也有情的历史,又把他推上了驶往探索宇宙空间的航船。应用物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三、四、五届代表……可谓是文武全才,纵横天地,嘉称连连,丹墀生辉,给祖上争了多少荣光!
关键时刻高瞻远瞩
“杨先生每天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有关航天的资料,因此,在世界航天技术发展上,不论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躲不过他的眼睛。”跟随杨嘉墀20年的秘书张学会敬佩地说。自从我国卫星、飞船的研制基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1968年成立后,杨嘉墀就来到了这里。
1983年,杨嘉墀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转任科技委副主任后,查阅并搜集了大量资料,完成了《我国应用卫星成就与效益分析》论文。论文对“七五”期间各种型号卫星所能获得的效益进行了估算(因为有许多效益是间接的),结论是:五年里,我国发射卫星8颗,总投资6亿元,而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为42亿元。
同年,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提出不久,就引起了杨嘉墀的关注。此后,日本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计划,欧共体提出了“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进一步引起了杨嘉墀的深思。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计划的相继制定登台不是偶然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动员国家力量,发展高科技,带动综合国力,占据世界制高点。一种越来越紧迫的危机感攫住了他的心:科学技术已经落后很大一段距离的中国该怎么办?
英雄所见略同。此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几位科学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由王大珩执笔、其他三人签名的国家发展高技术计划的倡议很快完成。
这份倡议一路绿灯,直呈中央,为国家制定“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计划的提出,充分展露出杨嘉墀等几位科学家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雄才大略,甚至可以说功盖天下。何以有此定论,请看1991年4月留于中国各新闻媒体的记载:
《人民日报》一版照片,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并肩进入会场,照片下的小标题:皓首献良策,四老志千里。简短的文字是:4月22日,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受到表扬。
《科技日报》头版头条评论员文章:1986年3月,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亲自肯定了由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发展高技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建议。
《光明日报》报道,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4月22日在京召开,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联合召开的这次会议旨在总结“七五”期间取得的重要进展和经验,审议“八五”期间“863计划”的战略设想和措施,表彰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大型画报《中华英才》以《“科技四老”与“863计划”》为题,详细介绍了四位老科学家的经历和“863计划”取得的成绩。文中写道:“作为个人,除了政治领袖,真正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并不多,但当今中国的四位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却催生出了我国的一个战略性发展计划,引发了我国一次历史性的科技大会战。”
“七五”期间“863计划”成果展也同时展出:两系杂交水稻技术栽种史上的突破,乙型肝炎疫苗的研究成功,试管牛犊的诞生,多智能机器人的进入应用,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快中子增殖堆关键技术取得的重大进展,秦山核电站的建成……累累硕果,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高技术发生的飞跃,功大者莫过于“四老”。
这位大科学家始终思路敏锐、朝气勃发,见微知著、洞察前沿。杨嘉墀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不断提出很多好建议。张学会说:“杨先生不断产生新想法、新见解。有了新建议,他就随手写成纸条。他提出的重大建议多是在纸条基础上形成的。”
2005年,事隔“863”倡议19年,杨嘉墀在86岁高龄时,又带头提出了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和五位院士一起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并得到了高度重视。
这是杨嘉墀在失去知觉之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许,在失去知觉那一刻,他没有遗憾了,因为最重大的事情,他已经办妥了。
祖国的需要就是最爱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杨嘉墀回国前,在美国就已经小有名气。
194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同事把他推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钱斯。钱斯看了他的毕业论文《富氏变换计装置及其应用》后,握着这名被美国同学称为“书生杨”的学生的手说:“我们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位曾参与制造出先进雷达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掌握制空权的专家没有看错人,当他把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光谱记录仪的自动化课题交给杨嘉墀后,副研究员杨嘉墀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快速模拟计算机和快速吸收光谱仪的研制。这一成功,不仅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还被专家定为“杨氏仪器”,至今还被当作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保存着。30年后,与杨嘉墀一起工作过的两个同事来中国,带给杨嘉墀的礼物中,就有一张杨嘉墀与“杨氏仪器”的合影。
杨嘉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展露出的才华,很快又被急于建立医学电子学研究室的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看中。该所与钱斯几经谈判,杨嘉墀又成了每周只能在该所工作3天的“生物医学电子学”的创始人。研究课题是用于神经生理试验的仪器——二色光谱仪和视网膜仿真仪,很可惜的是他善始没有善终。但那是迫不得已的,有什么比返回祖国机会的到来更重要呢?
1956年,祖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召唤。
祖国的号召令杨嘉墀心驰神往,祖国的召唤令他热血沸腾。面对美国的高薪挽留,在夫人徐斐的支持下,杨嘉墀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家中的一切,购买了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仪器: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1956年8月,杨嘉墀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出了名的好说话,接任务从不推三阻四,也从不说‘不’。”与杨嘉墀相交50年,也是1956年从美国回国的屠善澄院士说。最令屠善澄钦佩的是,为了国家需要,杨嘉墀几次改行,钻研了多个专业。仅大的转行就有两次:在国外读的是应用物理,回国后却先后长期致力于我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而且,由于祖国的需要,他不断给自己增添新的任务。不论哪个领域,只要他从事过研究,就都做出了成绩。
50年来,杨嘉墀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是我国一连串新兴学科领域的创建者;在涉足航天之前,已取得一连串的开拓性建树;进入航天领域,重大开创性贡献接连不断,尤其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早期论证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杨嘉墀1956年返回祖国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自动化所,杨嘉墀担任技术工具室主任。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杨嘉墀成为赴苏考察6人团成员。6人团考察后向中央提出建议:鉴于我国目前科技和工作状况,卫星工程上马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60年代初,我国探空火箭取得显著成绩,为卫星研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由杨嘉墀主持开展的导弹热应力和加热加载测试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
1963年,在原子弹研制已快进入尾声时,人们才发现整个试验还需要不少仪器。情况汇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力量不够抓科学院。”于是,杨嘉墀受命负责原子弹爆炸试验配套仪器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及地震动测量仪。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亮度是多少,国外的资料没有,国内更没做过这方面的模拟试验。爆炸时的亮度测不出来,摄影师便无法在拍摄时掌握曝光量。而有了火球温度测量仪,就可以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的亮度;摄影师在拍摄完后,可以根据实际亮度,在后期制作时,在暗房中对所拍的照片曝光量进行补偿。可以说,这台仪器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留下宝贵的原始资料,立下了大功。而仪器上使用的一个关键元器件——光电倍增管,竟是杨嘉墀返回祖国时带回的。如果进口,这台仪器的研制就成为“马后炮”了。
1969年杨嘉墀“靠边”到了北京假肢厂,为在礼花生产中因抢救国家财产而失去右臂和左手的王世芬研制假肢。不仅王世芬用上了,还出口远销海外。
1975年11月26日,甘肃省北部的大戈壁滩上,升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欢呼的人群里,人们没有见到杨嘉墀。在卫星运行一段时间后,杨嘉墀在渭南测控中心收到了卫星传回的一组不妙的气压过快下降的数据。这组数据告诉在场的人们,靠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来实现姿态控制的卫星,在转不完三天后,便会因氮气消耗殆尽而提前返回。
指挥卫星发射的钱学森,把杨嘉墀等专家请到了自己的房间,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如果不行,就放弃三天飞行计划,让卫星提前返回,因为中央已明确了一个态度:不管三天一天,发射出去再收回来,就是成功。
专家们一个接一个发言,都认为根据计算结果,运行三天的希望几乎是零。钱学森把目光转向一直低头用铅笔在纸上写着的杨嘉墀,点名要听听他的意见。杨嘉墀慢慢放下笔,用沉稳的语调说:“从我的计算判断,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地面温度高,空间温度低,卫星入轨后,因冷热悬殊,气压下降的速度就会加快,但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稳定下来。坚持三天问题不大,我的意见按原计划进行。”
钱学森拨通了通往中央的电话,卫星按原计划返回。决定作出后,杨嘉墀借着冬夜泛着寒气的月光,爬上了三四百米高的观测山顶。他后来回忆说:高度紧张状态下,并不觉得困和冷,一直守到天亮,气压完全稳定下来,才从山上下来。
11月29日,返回式卫星环绕地球转足了47圈,安稳着陆,国内外无不为之一震。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主持研制这颗卫星上的姿态控制系统的杨嘉墀和他的同事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冲击,停产闹革命;“靠边”,包括去造假肢,劳动“改造”当厨子……但对国家交给的工作,他依然执着。
把工作视作最爱的杨嘉墀,直到病倒之前,仍然保持着8点到办公室的习惯。他对工作总是来者不拒,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担心他会累垮身体。为这个,他们没少和他着急:“您别老答应,会把您累坏的!”话语里透出儿女般的担忧。慈眉善目的杨嘉墀说:“别怕,别怕!”事后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说:“唉,拿这个慈祥的老人真是没办法!”
“没什么,事是大家干的”
1981年9月20日,我国三星在同一时刻升空,杨嘉墀是实践二号卫星的总设计师。
1995年荣获陈嘉庚奖。
1999年9月18日,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受到国家科技最高奖赏,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挂上一枚光泽闪亮的金勋章。
……
熟悉他的人说,杨嘉墀总是由衷地认为,荣誉属于集体,属于群众。因此,他得了奖状、奖杯、奖章等,从不炫耀。面对祝贺、赞誉,他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连连说:“没什么,没什么。事是大家干的,我赶上了好时候。”
1959年参加各界“群英会”时,他这么说。
1984年获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时,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1995年获陈嘉庚信息科学奖时,1999年获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时,他这么说。
1999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还是这么说。
病倒前的2005年2月,杨嘉墀写了《我这五十年》一文,这是他少有的涉及自己的文章,没想到却成为绝笔。他这样写道:“我作为一名参与者,对于当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自强自立、团结协作,为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而拼搏的精神,至今难以忘怀。”他在文中满怀深情地呼唤:“我期望我国航天技术将不断占领科技高地,到21世纪中叶,能够与世界空间大国在航天科技领域并驾齐驱,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许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杨嘉墀获奖后,总是把应得的奖金全部捐赠给有关方面,用于支持科研事业。
6月11日12时45分,这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功勋科学家溘然长逝。
他走后,夫人徐斐说要接着完成他的两个遗愿:一个是把他刚出版的文集一一赠送科技界有关部门和人士,让他的科技成果、科技思想成为祖国的财富;一个是用他获得的最后一笔奖金--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20万元港币建立基金,奖励相关科技领域优秀的青年人才。
愿他的奖金和他的精神一起,激励更多的年轻学子创新创新再创新,为祖国的强盛而奋勇攻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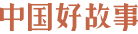

{{item.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