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读哈佛时,就有一些教授劝杜维明改行,因为在美国搞中国哲学几乎看不到前程,毕业后很可能连份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其他事情对我没有诱惑,我的兴趣在这里”。
每年的北京论坛都不会缺少杜维明的声音。2007年他以“人文奥运”为主题的演说提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视角——希腊文化和儒家文化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核心,这两种文化碰撞到一起怎样在差异中和谐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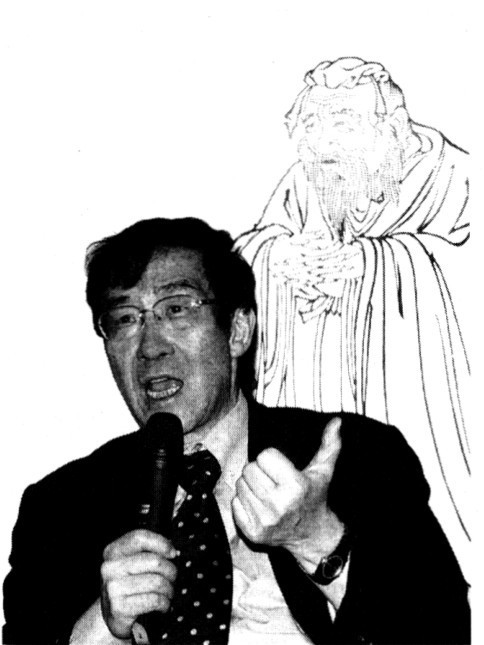
早在20年前,杜维明就预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潮,并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儒学研究和教学。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奔走于东西方之间,谈经论道,以至于很多人把他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世界、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信心符号。
“没有人要学儒学,你50年后再来吧”
杜维明的人生轨迹一直在东、西方之间转换。在西方,他要面对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在东方,则是新旧文化的冲突。
1978年,作为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明回大陆做学术交流。这是他9岁随父母到台湾后第一次回到大陆,时光流去29年,故乡早已是另一番天地。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文化界还没来得及休养生息,儒学在大陆几乎成了“绝学”。杜维明待了一个月,心里渐渐起了念头:要在大陆为儒学做点事。
此前的十多年中,杜维明一直在美国用英文向西方世界传播儒家文化。他越来越意识到,儒家文化如果不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就不可能在全世界形成气候。
20世纪80年代,中国致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整个文化界也处于思想解放的高峰。但那时知识分子更追捧外来的新思想,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并不重视。1985年,杜维明在北大开设儒家哲学课,有人却告诉他:中国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人要学这个,你应该50年后再来。
这样的心态让杜维明觉得似曾相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但他们是反对男权、父权、君权这些儒家的阴暗面。那时的人们太乐观了,以为只要抛弃传统包袱就能重新起步。可是传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不是说扔就能扔掉的。这是一个悖论,塑造我们的那些传统,都不要了,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民族强盛的那些理念、价值我们还没找到,这真正是落了空。”
然而,一位叫王轩的山东老工人让杜维明看到了希望。老人自己出钱从民间把孟庙流失的砖头一块一块地买回来,重建孟庙。1994年,老人给远在美国的杜维明写信,邀请他参加山东邹县“孟子学术会议”。杜维明在第一时间从波士顿飞抵北京,昼夜不停赶到济南,等他到达邹县已是凌晨4点。准时站到会议的讲台上,杜维明全然忘了疲惫,因为儒家文化在民间复活的迹象让他兴奋不已。
“这也是我的社会”
引领杜维明走上儒学之路的是高中老师周文杰。周文杰是当时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他将杜维明引荐给牟宗三。于是杜维明有时间便跑到台湾师大去听牟宗三的课,师徒众人还一起结伴到户外品茶论学,谈经辩难。
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下,杜维明从儒学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旁人会认为我这几十年一帆风顺,从台湾到美国,在普林斯顿、伯克利、哈佛之间走来走去。其实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认同,别人经常说:你在搞儒学,脑子有问题啊?”早在读哈佛时,就有一些教授劝杜维明改行,因为在美国搞中国哲学几乎看不到前程,毕业后很可能连份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其他事情对我没有诱惑,我的兴趣在这里”。
和杜维明交谈,很快能发现他对中国现状了解得极其广泛而深刻。他这一代的海外学者,大多是在海外生活多年,回到大陆讲学,怎么讲都隔了一层。笔者不禁问他:“你怎么这么了解我们的社会?”他立即反驳:“不仅仅是你们的,这也是我的社会。”
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他才会忧虑。“现在中国社会的浮躁非常严重!三四十岁的精英分子,英文非常好但是文化底蕴非常差,而且很傲慢。有一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邀请中国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去研讨,他张口就问:是我跟他们学还是他们跟我学?还有一次在联合国做演讲,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限定了,国际上的著名学者都提前写好发言稿,把握时间。可是我们的一位年轻学者没有做任何书面准备,上台先花五分钟‘热身’,到他真正要讲的时候没有时间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真正想在文化上有所创见的年轻人太少。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金钱、权力、名誉、公益、智慧,让大学生们选择这些要素在人生中的排序,美国是公益、智慧在前。中国大学生的答案什么样,大概我们猜得到。”
他的忧虑常常是具体的,从环境到房价,从汽车数量到资源消耗。在杜维明的定义中,埋首于书桌前是学者的权利,而担当天下则是义务和责任。
文明融合大于冲突
在“文明冲突论”泛滥的今天,杜维明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既要承认对方的存在,尊重其存在的价值和条件,又应具备文明对话主体的批判性。
20世纪90年代,萨缪尔·亨廷顿发表了轰动全球的《文明的冲突》,认为冲突、威胁势在必然;但杜维明几乎同时提出“21世纪是文明对话的世纪”。他认为,“文明冲突说”是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亨廷顿认为,直接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是伊斯兰世界,但是间接的威胁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中国。其实,“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始于此处。
杜维明告诉笔者,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的,文明不能单以器物论高下。当代中国人受西方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已经习惯于把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作为衡量民族文明优劣的标准。所以才会问:“文明之间怎么对话?”大家认为低水平文明学习高水平文明是天经地义的,高级文明能从低级文明中学到什么呢?
“实际上文明的发达程度不能简单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来衡量。比如19世纪初,法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宗教和艺术发展远远超出法国,其绘画艺术直接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创作风格。”他说,“所以不同的文明间需要学习,需要对话。”
他认为,中国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应当成为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强人所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另一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发展就一定要让别人也能发展。(摘编自《先生们》,现代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